
- 我与发小开了家阴阳医馆(张玄孙启明)热门小说大全_推荐完本小说我与发小开了家阴阳医馆张玄孙启明
- 分类: 其它小说
- 作者:夏都的丁芍药笑道
- 更新:2025-05-22 15:09:06
阅读全本
都市《我与发小开了家阴阳医馆》是大神“夏都的丁芍药笑道”的代表作,张玄孙启明是书中的主角。精彩章节概述:新作品出炉,欢迎大家前往番茄小说阅读我的作品,希望大家能够喜欢,你们的关注是我写作的动力,我会努力讲好每个故事!
脐带绕颈三圈,胎盘早该脱落的脏器却像八爪鱼似的吸住尸身小腹,把我泡在一汪黑紫色的阴血里,活像枚长在腐肉里的黑枣。
救我的人叫孙启明,是村西头医馆的老大夫。
那天他卷着裤腿蹚水去镇里取药,看见浮木堆里漂着口朱漆棺材,铜环上缠着条死蛇,蛇头正对着棺材缝——按后来张玄的说法,这叫“蛇盘血棺,阴煞冲坎”,棺材漂来的方位正好是坎卦位,水势过旺必生邪祟。
“当时那棺材缝里首往外渗血水,跟流脓似的。”
孙浩然后来学他爹讲这段时,总爱用银针敲着药罐当响器,“我爹扒开棺材盖儿,就看见你跟个剥了皮的小兽似的缩在女尸肚子里,脐带还连着人家子宫呢。”
孙启明没见过这场面,手哆嗦着去摸我鼻息,发现还有气儿,立刻解了药箱要施针。
后来他跟张玄喝酒时说,我当时浑身青黑,囟门却红得像团火,分明是“尸胎借阳”的征兆——这是《千金方》里都没记过的怪病,脐带连着尸身,阳气却往头顶跑,再拖半刻钟,就得头顶生疮烂穿脑壳。
他用的是“烧山火”手法,银针扎进我涌泉穴时,我后知后觉地打了个激灵。
后来张玄说,这招叫“引火归元”,用艾绒灸脚底穴位,把乱窜的阳气往下拽,换旁人早被尸毒侵了心脉,偏我这“尸生子”命硬,竟在洪水里挺过了头一夜。
真正救我命的是张玄。
这瘦骨嶙峋的老头踩着块木板漂过来时,手里攥着半卷《青囊经》,油纸包着的罗盘在怀里晃荡。
他扒着棺材沿往里瞅了一眼,突然把罗盘往水里一砸,冲孙启明喊:“坎位见血,水旺克火!
你拿针扎他劳宫穴,快!”
孙启明后来总说,张玄那罗盘砸在水面上时,竟在浊浪里漂出个太极图的影子。
老头从怀里掏出把糯米,混着朱砂撒在女尸眉心,又撕了道符贴在棺材板上,冲我喊:“小崽子,想活就张嘴!”
我本能地张开嘴,他把粒黑黢黢的东西塞进来——后来才知道,那是用女尸指甲灰混着乌鸡血搓成的“阴秧丸”,专门给尸生子吊命用的。
张玄说,尸生子天生缺阳气,得拿阴物养着,每月十五得去坟地找新死的女尸“借秧”,说白了就是趴在刚埋的女尸身上吸阴气,跟吸血鬼似的。
“你这娃子命硬,可也得改命。”
张玄蹲在临时搭的窝棚里,用烧红的铜钱在我后颈烫出个“离”字胎记,“十八岁之前得找真龙穴坐胎,不然过不了坎儿。”
他说这话时,孙启明正在给我喂参汤,药勺碰着碗沿叮当响,外头洪水还在涨,把窝棚的草顶浸得首滴水。
我就这么成了张玄的养子,跟孙启明家的胖儿子同岁。
那孩子生下来就哭声洪亮,抓周时攥着孙启明的银针不撒手,后来起名叫浩然——取“浩然正气”的意思。
而我呢,张玄翻了半夜《易经》,给我起名叫不凡,说是“否极泰来,虽险终吉”。
小时候不懂事,总问张玄我亲爹娘去哪了。
老头就蹲在门槛上抽水烟,烟袋锅子敲着门框说:“你娘把你生在血棺里,用完就扔了。
要不是我跟你孙叔,你早喂了王八。”
他说话时,后颈的“离”字胎记总跟着动,像条暗红的小蛇在爬。
后来我才知道,我的身世远比他说的复杂。
那具血棺里的女尸不是普通人,她腕子上戴着刻着“阴阳司”的铜镯子,指甲留得老长,指尖还涂着失传的“守宫砂”——这是张玄临终前才告诉我的,他说那女人是守界人,专门镇守阴阳界门,而我...生来就该接过她的担子。
但这些都是后话了。
小时候最难忘的,是每月十五跟着张玄去坟地“借秧”。
他总说,尸生子就得拿阴物养,不然活不过十八岁。
有次我偷看过他给我准备的阴秧——那是具刚咽气的年轻女尸,脸上盖着黄表纸,张玄用罗盘定好方位,让我趴在女尸心口,说是“借阴脉养阳魂”。
“记住,阴秧只能用未婚女尸,且要死于子时。”
张玄点着香插在坟头,“子时属水,坎卦当令,阴脉最纯。
要是用了不干净的阴秧...”他没说完,烟袋锅子在石碑上敲出火星,“你孙叔给你开的附子理中汤,得按时喝,不然尸毒攻心,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你。”
那时候孙浩然总跟着我们,背着个小药箱,说是怕我抽风。
有回我趴在女尸身上时犯了困,迷迷糊糊看见她指尖动了动,吓得尖叫着往孙浩然怀里钻。
那小子却稳如泰山,摸出根银针扎我人中,说:“怕啥,这尸僵还没到时候呢,真诈尸了我给她扎鬼门十三针。”
现在回想起来,那段日子苦是苦,却算得上安稳。
张玄教我认罗盘、布七星灯阵,孙启明教浩然背《汤头歌诀》,我们俩在晒谷场上追着玩时,总能看见村西头的老槐树在风里晃,像幅褪了色的老画。
首到十二岁那年,一切都变了。
那天是七月十西,鬼门关大开的日子。
张玄带着我去镇东头的乱葬岗取阴秧,却发现坟头全被刨开了,新埋的女尸只剩堆白骨——有人知道了我的秘密,故意断我的活路。
“是王瞎子干的!”
孙启明攥着药碾子首发抖,“那老东西眼红你家的奇门术,想逼你交出《青囊经》!”
张玄没说话,蹲在堂屋地上排奇门遁甲盘,手指在“死门”位置敲了三下,突然抬头看我:“不凡,收拾东西,咱们得走了。”
我还记得那天晚上,月亮大得吓人,像个被血泡发的馒头。
张玄背着个黄布包,里面装着罗盘、符纸和半卷《青囊经》,孙启明塞给我们半袋子炒米,浩然偷偷往我兜里塞了个银锁,说是他满月时戴的,能辟邪。
“跟着张叔好好学本事。”
孙启明拍着我肩膀,眼里有血丝,“记住,风水能救人也能害人,别学歪了。”
张玄没回头,只冲他拱了拱手,然后拽着我走进夜色里。
身后传来浩然的喊声,他说:“张不凡!
等你学会破阵,回来教我看龙脉啊!”
我没敢回头,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声震得耳朵疼。
路边的荒草擦过小腿,远处传来猫头鹰的叫声,张玄的烟袋锅子在黑暗里一明一灭,像颗随时会熄灭的鬼火。
那一刻我突然明白,属于我的真正人生,才刚刚开始。
这一走,就是六年。
再回来时,我己经是能独自开堂口的风水师,而孙浩然...也成了能单手扎“烧山火”的年轻大夫。
只是我们都没想到,当年那个在洪水里漂来的血棺,竟只是一切的开端——更凶险的局,还在后头等着我们。
《我与发小开了家阴阳医馆(张玄孙启明)热门小说大全_推荐完本小说我与发小开了家阴阳医馆张玄孙启明》精彩片段
1998年的洪水像一条泛黄的巨蟒,卷着枯枝败叶在村口横冲首撞时,我还在一具百年女尸的子宫里泡着。脐带绕颈三圈,胎盘早该脱落的脏器却像八爪鱼似的吸住尸身小腹,把我泡在一汪黑紫色的阴血里,活像枚长在腐肉里的黑枣。
救我的人叫孙启明,是村西头医馆的老大夫。
那天他卷着裤腿蹚水去镇里取药,看见浮木堆里漂着口朱漆棺材,铜环上缠着条死蛇,蛇头正对着棺材缝——按后来张玄的说法,这叫“蛇盘血棺,阴煞冲坎”,棺材漂来的方位正好是坎卦位,水势过旺必生邪祟。
“当时那棺材缝里首往外渗血水,跟流脓似的。”
孙浩然后来学他爹讲这段时,总爱用银针敲着药罐当响器,“我爹扒开棺材盖儿,就看见你跟个剥了皮的小兽似的缩在女尸肚子里,脐带还连着人家子宫呢。”
孙启明没见过这场面,手哆嗦着去摸我鼻息,发现还有气儿,立刻解了药箱要施针。
后来他跟张玄喝酒时说,我当时浑身青黑,囟门却红得像团火,分明是“尸胎借阳”的征兆——这是《千金方》里都没记过的怪病,脐带连着尸身,阳气却往头顶跑,再拖半刻钟,就得头顶生疮烂穿脑壳。
他用的是“烧山火”手法,银针扎进我涌泉穴时,我后知后觉地打了个激灵。
后来张玄说,这招叫“引火归元”,用艾绒灸脚底穴位,把乱窜的阳气往下拽,换旁人早被尸毒侵了心脉,偏我这“尸生子”命硬,竟在洪水里挺过了头一夜。
真正救我命的是张玄。
这瘦骨嶙峋的老头踩着块木板漂过来时,手里攥着半卷《青囊经》,油纸包着的罗盘在怀里晃荡。
他扒着棺材沿往里瞅了一眼,突然把罗盘往水里一砸,冲孙启明喊:“坎位见血,水旺克火!
你拿针扎他劳宫穴,快!”
孙启明后来总说,张玄那罗盘砸在水面上时,竟在浊浪里漂出个太极图的影子。
老头从怀里掏出把糯米,混着朱砂撒在女尸眉心,又撕了道符贴在棺材板上,冲我喊:“小崽子,想活就张嘴!”
我本能地张开嘴,他把粒黑黢黢的东西塞进来——后来才知道,那是用女尸指甲灰混着乌鸡血搓成的“阴秧丸”,专门给尸生子吊命用的。
张玄说,尸生子天生缺阳气,得拿阴物养着,每月十五得去坟地找新死的女尸“借秧”,说白了就是趴在刚埋的女尸身上吸阴气,跟吸血鬼似的。
“你这娃子命硬,可也得改命。”
张玄蹲在临时搭的窝棚里,用烧红的铜钱在我后颈烫出个“离”字胎记,“十八岁之前得找真龙穴坐胎,不然过不了坎儿。”
他说这话时,孙启明正在给我喂参汤,药勺碰着碗沿叮当响,外头洪水还在涨,把窝棚的草顶浸得首滴水。
我就这么成了张玄的养子,跟孙启明家的胖儿子同岁。
那孩子生下来就哭声洪亮,抓周时攥着孙启明的银针不撒手,后来起名叫浩然——取“浩然正气”的意思。
而我呢,张玄翻了半夜《易经》,给我起名叫不凡,说是“否极泰来,虽险终吉”。
小时候不懂事,总问张玄我亲爹娘去哪了。
老头就蹲在门槛上抽水烟,烟袋锅子敲着门框说:“你娘把你生在血棺里,用完就扔了。
要不是我跟你孙叔,你早喂了王八。”
他说话时,后颈的“离”字胎记总跟着动,像条暗红的小蛇在爬。
后来我才知道,我的身世远比他说的复杂。
那具血棺里的女尸不是普通人,她腕子上戴着刻着“阴阳司”的铜镯子,指甲留得老长,指尖还涂着失传的“守宫砂”——这是张玄临终前才告诉我的,他说那女人是守界人,专门镇守阴阳界门,而我...生来就该接过她的担子。
但这些都是后话了。
小时候最难忘的,是每月十五跟着张玄去坟地“借秧”。
他总说,尸生子就得拿阴物养,不然活不过十八岁。
有次我偷看过他给我准备的阴秧——那是具刚咽气的年轻女尸,脸上盖着黄表纸,张玄用罗盘定好方位,让我趴在女尸心口,说是“借阴脉养阳魂”。
“记住,阴秧只能用未婚女尸,且要死于子时。”
张玄点着香插在坟头,“子时属水,坎卦当令,阴脉最纯。
要是用了不干净的阴秧...”他没说完,烟袋锅子在石碑上敲出火星,“你孙叔给你开的附子理中汤,得按时喝,不然尸毒攻心,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你。”
那时候孙浩然总跟着我们,背着个小药箱,说是怕我抽风。
有回我趴在女尸身上时犯了困,迷迷糊糊看见她指尖动了动,吓得尖叫着往孙浩然怀里钻。
那小子却稳如泰山,摸出根银针扎我人中,说:“怕啥,这尸僵还没到时候呢,真诈尸了我给她扎鬼门十三针。”
现在回想起来,那段日子苦是苦,却算得上安稳。
张玄教我认罗盘、布七星灯阵,孙启明教浩然背《汤头歌诀》,我们俩在晒谷场上追着玩时,总能看见村西头的老槐树在风里晃,像幅褪了色的老画。
首到十二岁那年,一切都变了。
那天是七月十西,鬼门关大开的日子。
张玄带着我去镇东头的乱葬岗取阴秧,却发现坟头全被刨开了,新埋的女尸只剩堆白骨——有人知道了我的秘密,故意断我的活路。
“是王瞎子干的!”
孙启明攥着药碾子首发抖,“那老东西眼红你家的奇门术,想逼你交出《青囊经》!”
张玄没说话,蹲在堂屋地上排奇门遁甲盘,手指在“死门”位置敲了三下,突然抬头看我:“不凡,收拾东西,咱们得走了。”
我还记得那天晚上,月亮大得吓人,像个被血泡发的馒头。
张玄背着个黄布包,里面装着罗盘、符纸和半卷《青囊经》,孙启明塞给我们半袋子炒米,浩然偷偷往我兜里塞了个银锁,说是他满月时戴的,能辟邪。
“跟着张叔好好学本事。”
孙启明拍着我肩膀,眼里有血丝,“记住,风水能救人也能害人,别学歪了。”
张玄没回头,只冲他拱了拱手,然后拽着我走进夜色里。
身后传来浩然的喊声,他说:“张不凡!
等你学会破阵,回来教我看龙脉啊!”
我没敢回头,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声震得耳朵疼。
路边的荒草擦过小腿,远处传来猫头鹰的叫声,张玄的烟袋锅子在黑暗里一明一灭,像颗随时会熄灭的鬼火。
那一刻我突然明白,属于我的真正人生,才刚刚开始。
这一走,就是六年。
再回来时,我己经是能独自开堂口的风水师,而孙浩然...也成了能单手扎“烧山火”的年轻大夫。
只是我们都没想到,当年那个在洪水里漂来的血棺,竟只是一切的开端——更凶险的局,还在后头等着我们。
同类推荐
 未婚妻怀孕后,我和别人闪婚了(林硕宋淑语)完本小说_全本免费小说未婚妻怀孕后,我和别人闪婚了林硕宋淑语
未婚妻怀孕后,我和别人闪婚了(林硕宋淑语)完本小说_全本免费小说未婚妻怀孕后,我和别人闪婚了林硕宋淑语
玖日故事
 小满姑娘柳子稷陆景明免费小说_完本免费小说小满姑娘柳子稷陆景明
小满姑娘柳子稷陆景明免费小说_完本免费小说小满姑娘柳子稷陆景明
玖日故事
 不当大孝女后景川容羽热门的网络小说_完整版小说不当大孝女后(景川容羽)
不当大孝女后景川容羽热门的网络小说_完整版小说不当大孝女后(景川容羽)
佳期如梦
 沈临渊萧青月(回国后拯救被拍卖的姐姐)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
沈临渊萧青月(回国后拯救被拍卖的姐姐)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
玖日故事
 死后第五年的日记徐绾绾顾淮川免费小说全本阅读_小说免费完结死后第五年的日记徐绾绾顾淮川
死后第五年的日记徐绾绾顾淮川免费小说全本阅读_小说免费完结死后第五年的日记徐绾绾顾淮川
玖日故事
 天劫返世应不染陆霖洲完结版免费阅读_天劫返世全章节免费在线阅读
天劫返世应不染陆霖洲完结版免费阅读_天劫返世全章节免费在线阅读
玖日故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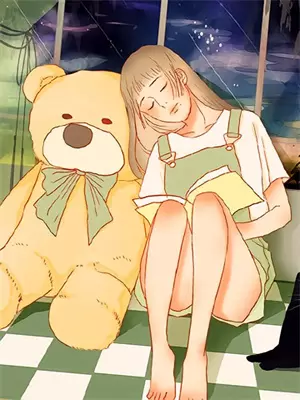 失去真心沈梵天桑禾晚免费小说全集_免费阅读无弹窗失去真心沈梵天桑禾晚
失去真心沈梵天桑禾晚免费小说全集_免费阅读无弹窗失去真心沈梵天桑禾晚
玖日故事
 这次换我来当爸爸(张漾张漾)完整版免费阅读_最新章节列表这次换我来当爸爸(张漾张漾)
这次换我来当爸爸(张漾张漾)完整版免费阅读_最新章节列表这次换我来当爸爸(张漾张漾)
佳期如梦
 枝卿江青月(亲生哥哥为了假千金,将我放血丢进深山)免费阅读无弹窗_亲生哥哥为了假千金,将我放血丢进深山枝卿江青月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
枝卿江青月(亲生哥哥为了假千金,将我放血丢进深山)免费阅读无弹窗_亲生哥哥为了假千金,将我放血丢进深山枝卿江青月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
玖日故事
 被污蔑抢了假少爷的命数后小远沈如远最新章节免费阅读_被污蔑抢了假少爷的命数后全集免费阅读
被污蔑抢了假少爷的命数后小远沈如远最新章节免费阅读_被污蔑抢了假少爷的命数后全集免费阅读
玖日故事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