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- 我与发小开了家阴阳医馆张玄孙启明小说完结免费_最新章节列表我与发小开了家阴阳医馆(张玄孙启明)
- 分类: 其它小说
- 作者:夏都的丁芍药笑道
- 更新:2025-05-22 15:09:09
阅读全本
都市《我与发小开了家阴阳医馆》是大神“夏都的丁芍药笑道”的代表作,张玄孙启明是书中的主角。精彩章节概述:新作品出炉,欢迎大家前往番茄小说阅读我的作品,希望大家能够喜欢,你们的关注是我写作的动力,我会努力讲好每个故事!
张玄用三块青砖摆成三才阵,罗盘搁在中间,针尖首指北方。
我蹲在旁边看他画符,黄表纸上的朱砂字像活过来似的,在月光下泛着腥红。
“记住,阴宅看‘龙、穴、砂、水’。”
他用符纸引燃艾草,浓烟裹着火星子往北方飘,“龙是山脉走势,穴是藏风聚气处,砂是西周护山,水是明堂活水。
今晚这山神庙,龙从东北来,却被巨石截断,叫‘青龙折足’,葬在这里的人后代必出瘸子。”
我似懂非懂,摸出孙浩然给的银锁攥在手心。
这六年里,张玄带着我走南闯北,睡过义庄、破庙,也在坟地里守过通宵。
他教我用罗盘测“分金定穴”,说针尖偏一分,福祸差千里;教我认《青囊经》里的蝌蚪文,讲“气乘风则散,界水则止”的道理;最紧要的,是开天眼的法子。
“开天眼不是真开眼,是让魂灵出窍三分。”
十五岁那年中秋,他带我上岳麓山,在爱晚亭外摆了童子尿浸过的柏木盆。
月亮升到正南时,他往盆里撒了把夜明砂,水面立刻浮起密密麻麻的光点,“盯着看,看到光点聚成线,便是‘天眼初开’。”
我盯得眼眶发酸,忽然看见月光里游过几团白雾,有的像人,有的像兽,在树梢间飘来荡去。
张玄说那是“山精野魄”,开天眼初期能见灵体轮廓,等练到能辨气场颜色,才算入门。
“颜色怎么辨?”
我揉着眼问。
他往盆里滴了滴公鸡血,水面突然泛起红光,像泼了碗朱砂:“赤色为煞,青色为生,白色主孝。
若见金色气场,必是大贵之地;见黑色...便是阴魂不散。”
这些年,我跟着他破过最险的局,是长沙城郊的“黄泉煞”阴宅。
那家人连续三代活不过西十,张玄用罗盘测出墓穴坐向犯了“坤山艮向”,正冲“黄泉煞”位。
他教我用“五弊三缺”里的“改穴法”,半夜刨开坟头,在棺木下垫了三层青砖,又在东南方种了棵银杏树——“金克木,木克土,土克水,水克火,火克金”,五行连环相克,才算破了这局。
孙浩然的消息全靠书信往来。
他在信里说,孙启明教他认《伤寒论》,头一年光背汤头就背得满嘴燎泡;又说他学会了“透天凉”针法,能让人三伏天里出冷汗;还画过一张脉案给我看,说某户人家的儿子面黄体瘦,脉沉细而迟,他断是“宅中阴气过盛,木气受克”,建议在院子里种梧桐——这分明是把中医和风水结合了。
“那小子是块行医的料。”
张玄看过信后哼了声,“但风水医理本就相通,你看这脉案,肝属木,肺属金,金克木,若住宅西方有煞,必伤肝木。
他让种梧桐,取‘梧桐属木,引东方生气’之意,倒也对症。”
十二岁到十八岁,我跟着张玄走了七个省,破了三十多桩阴宅阳宅的案子。
每到一地,他必带我去看当地的名坟古宅,用罗盘测方位,讲“三年寻龙,十年点穴”的道理。
有回在武当山,他指着七十二峰说:“龙分九势,这里是‘回龙顾祖’,主出帝王将相。”
又指着山涧里的瀑布:“水绕玄武,是为‘金城环抱’,葬在此处,后代必富甲一方。”
但最让我心惊的,是他讲起我的身世。
“你娘是阴阳司最后一任守界人。”
某天夜里,他突然没头没脑地说,手里拨弄着从血棺里取出的铜镯子,“阴阳司镇守界门三百年,每任守界人都要以自身为阵眼。
你体内的真龙之气,就是她用命引来的龙脉之气。”
我摸着后颈的“离”字胎记,问:“那界门...是什么?”
他沉默许久,往火里添了根柴:“是阴阳两界的门缝。
千年前阴兵借道、百鬼夜行,都是界门不稳的征兆。
你娘用风水大阵镇住界门,自己却被反噬,只能把你寄养在血棺里...”他没说完,烟袋锅子敲在铜镯子上,发出沉闷的响声。
远处传来猫头鹰的叫声,我忽然想起孙浩然的信,他说镇上来了个游方道士,瞧着像寻仇的。
张玄猛地抬头,罗盘指针突然狂转,针尖首指南方——那是赵家村的方向。
“该回去了。”
他掐灭烟袋,“你十八岁改命的日子,就在眼前了。”
回到赵家村时,正是七月初七。
村口的老槐树被雷劈了半边,露出焦黑的树干,像道狰狞的伤疤。
孙启明的医馆还开着,门上挂着“悬壶济世”的匾额,只是金字褪了色。
“你们可算回来了。”
孙启明看见我们时,手里的药勺都在抖,“浩然这半年总说心口疼,我瞧着...像是中了阴煞。”
张玄眉头一皱,掏出罗盘在院子里走了几步,针尖突然指向井台:“这井...不对劲。”
我跟着看过去,井口结着青苔,水面漂着片枯叶,在夕阳下泛着死气。
“去年冬天,有个外乡女子投了井。”
孙启明低声说,“捞上来时肚子己经大了,像是有七个月身孕。
我想着可怜,就埋在西山坡了...”张玄蹲在井边,用符纸蘸了水在井口画圈,符纸突然起火:“井底有‘血湖煞’,那女子是含冤而死,肚子里的孩子成了‘胎煞’,正冲医馆的‘生气位’。
浩然属木,木遇阴煞,必伤肝脾。”
我想起孙浩然信里说的“心口疼”,忙问:“怎么解?”
张玄从包里取出七枚铜钱,按北斗七星摆放在井台上,又烧了道“五雷符”:“今晚子时,你下井把那女尸挖出来,移到向阳处安葬。
记得用朱砂在她眉心点‘往生印’,再给胎儿超度...”他话没说完,医馆里突然传来瓷器碎裂的声音。
我们冲进屋,只见孙浩然扶着药柜站在地上,脸色煞白如纸,手里还攥着块碎瓷片——他的掌心被划开道口子,血珠滴在青砖上,竟凝成了紫黑色。
“浩然!”
我冲过去按住他的手,触到他脉搏时心里一惊——那脉搏虚浮无根,像片随时会被吹走的落叶。
孙启明拿出银针要扎“内关穴”,张玄却拦住他,翻开孙浩然的眼皮看了看:“不用针,是阴煞入体。
去拿附子理中汤,再加三钱朱砂...”我望着窗外渐暗的天色,手心全是冷汗。
六年未见,曾经追着我跑的胖小子如今瘦得脱了形,眼窝深陷,嘴唇发青,分明是被阴煞缠了半年。
张玄说的没错,这趟回来,怕是有场硬仗要打了。
子时三刻,我蹲在井边,手里攥着洛阳铲。
张玄在井口摆了盏七星灯,灯芯跳动不定,映得他脸色铁青:“下去后先找尸身,若见胎儿缠着脐带,立刻用黑狗血泼上去。
记住,卯时前必须完事,否则...后患无穷。”
我点头,握紧铲子跳进井里。
井底淤泥没到膝盖,腐臭味熏得人作呕。
借着月光,我看见角落里蜷缩着具女尸,长发遮住脸,肚子高高隆起,果然如孙启明所说。
刚走近两步,突然听见“咔嚓”一声——是骨骼错位的声音。
女尸的头缓缓转过来,眼窝深陷,嘴角咧开,露出青白的牙齿。
我握紧铲子,指甲掐进掌心——这是“僵尸初醒”的征兆,若让她起了尸,今晚谁也别想活着出去。
“得罪了。”
我默念一句,抡起铲子砸向她心口。
淤泥溅起,露出她胸口插着的半截剪刀——原来她是用剪刀刺进心脏而死,难怪怨气不散,化为胎煞。
“天圆地方,律令九章...”我念着张玄教的镇魂咒,用黑狗血泼在她眉心,“阴魂归位,勿扰生民...”女尸突然发出低吟,肚子里鼓起个小包,像有什么东西在动。
我浑身冷汗,颤抖着摸出朱砂,正要往她肚子上画符,井口突然传来张玄的喊声:“不凡!
快上来!
有人来了!”
我抬头望去,只见月光里晃过几个黑影,手里提着锄头、镰刀,正是赵家村的村民。
领头的是王瞎子,他拄着拐杖,阴恻恻地笑:“张不凡,可算等到你了...”身后传来布料撕裂的声音,我转头一看,女尸的肚子己经裂开,露出半只青紫色的小手。
井外的脚步声越来越近,张玄的七星灯突然熄灭,黑暗中传来罗盘摔碎的声音——这下糟了,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
这一夜,注定无眠。
而我和孙浩然的命运,也在这口阴井里,悄然埋下了更深的伏笔。
《我与发小开了家阴阳医馆张玄孙启明小说完结免费_最新章节列表我与发小开了家阴阳医馆(张玄孙启明)》精彩片段
离开赵家村的第一夜,我们在山神庙过夜。张玄用三块青砖摆成三才阵,罗盘搁在中间,针尖首指北方。
我蹲在旁边看他画符,黄表纸上的朱砂字像活过来似的,在月光下泛着腥红。
“记住,阴宅看‘龙、穴、砂、水’。”
他用符纸引燃艾草,浓烟裹着火星子往北方飘,“龙是山脉走势,穴是藏风聚气处,砂是西周护山,水是明堂活水。
今晚这山神庙,龙从东北来,却被巨石截断,叫‘青龙折足’,葬在这里的人后代必出瘸子。”
我似懂非懂,摸出孙浩然给的银锁攥在手心。
这六年里,张玄带着我走南闯北,睡过义庄、破庙,也在坟地里守过通宵。
他教我用罗盘测“分金定穴”,说针尖偏一分,福祸差千里;教我认《青囊经》里的蝌蚪文,讲“气乘风则散,界水则止”的道理;最紧要的,是开天眼的法子。
“开天眼不是真开眼,是让魂灵出窍三分。”
十五岁那年中秋,他带我上岳麓山,在爱晚亭外摆了童子尿浸过的柏木盆。
月亮升到正南时,他往盆里撒了把夜明砂,水面立刻浮起密密麻麻的光点,“盯着看,看到光点聚成线,便是‘天眼初开’。”
我盯得眼眶发酸,忽然看见月光里游过几团白雾,有的像人,有的像兽,在树梢间飘来荡去。
张玄说那是“山精野魄”,开天眼初期能见灵体轮廓,等练到能辨气场颜色,才算入门。
“颜色怎么辨?”
我揉着眼问。
他往盆里滴了滴公鸡血,水面突然泛起红光,像泼了碗朱砂:“赤色为煞,青色为生,白色主孝。
若见金色气场,必是大贵之地;见黑色...便是阴魂不散。”
这些年,我跟着他破过最险的局,是长沙城郊的“黄泉煞”阴宅。
那家人连续三代活不过西十,张玄用罗盘测出墓穴坐向犯了“坤山艮向”,正冲“黄泉煞”位。
他教我用“五弊三缺”里的“改穴法”,半夜刨开坟头,在棺木下垫了三层青砖,又在东南方种了棵银杏树——“金克木,木克土,土克水,水克火,火克金”,五行连环相克,才算破了这局。
孙浩然的消息全靠书信往来。
他在信里说,孙启明教他认《伤寒论》,头一年光背汤头就背得满嘴燎泡;又说他学会了“透天凉”针法,能让人三伏天里出冷汗;还画过一张脉案给我看,说某户人家的儿子面黄体瘦,脉沉细而迟,他断是“宅中阴气过盛,木气受克”,建议在院子里种梧桐——这分明是把中医和风水结合了。
“那小子是块行医的料。”
张玄看过信后哼了声,“但风水医理本就相通,你看这脉案,肝属木,肺属金,金克木,若住宅西方有煞,必伤肝木。
他让种梧桐,取‘梧桐属木,引东方生气’之意,倒也对症。”
十二岁到十八岁,我跟着张玄走了七个省,破了三十多桩阴宅阳宅的案子。
每到一地,他必带我去看当地的名坟古宅,用罗盘测方位,讲“三年寻龙,十年点穴”的道理。
有回在武当山,他指着七十二峰说:“龙分九势,这里是‘回龙顾祖’,主出帝王将相。”
又指着山涧里的瀑布:“水绕玄武,是为‘金城环抱’,葬在此处,后代必富甲一方。”
但最让我心惊的,是他讲起我的身世。
“你娘是阴阳司最后一任守界人。”
某天夜里,他突然没头没脑地说,手里拨弄着从血棺里取出的铜镯子,“阴阳司镇守界门三百年,每任守界人都要以自身为阵眼。
你体内的真龙之气,就是她用命引来的龙脉之气。”
我摸着后颈的“离”字胎记,问:“那界门...是什么?”
他沉默许久,往火里添了根柴:“是阴阳两界的门缝。
千年前阴兵借道、百鬼夜行,都是界门不稳的征兆。
你娘用风水大阵镇住界门,自己却被反噬,只能把你寄养在血棺里...”他没说完,烟袋锅子敲在铜镯子上,发出沉闷的响声。
远处传来猫头鹰的叫声,我忽然想起孙浩然的信,他说镇上来了个游方道士,瞧着像寻仇的。
张玄猛地抬头,罗盘指针突然狂转,针尖首指南方——那是赵家村的方向。
“该回去了。”
他掐灭烟袋,“你十八岁改命的日子,就在眼前了。”
回到赵家村时,正是七月初七。
村口的老槐树被雷劈了半边,露出焦黑的树干,像道狰狞的伤疤。
孙启明的医馆还开着,门上挂着“悬壶济世”的匾额,只是金字褪了色。
“你们可算回来了。”
孙启明看见我们时,手里的药勺都在抖,“浩然这半年总说心口疼,我瞧着...像是中了阴煞。”
张玄眉头一皱,掏出罗盘在院子里走了几步,针尖突然指向井台:“这井...不对劲。”
我跟着看过去,井口结着青苔,水面漂着片枯叶,在夕阳下泛着死气。
“去年冬天,有个外乡女子投了井。”
孙启明低声说,“捞上来时肚子己经大了,像是有七个月身孕。
我想着可怜,就埋在西山坡了...”张玄蹲在井边,用符纸蘸了水在井口画圈,符纸突然起火:“井底有‘血湖煞’,那女子是含冤而死,肚子里的孩子成了‘胎煞’,正冲医馆的‘生气位’。
浩然属木,木遇阴煞,必伤肝脾。”
我想起孙浩然信里说的“心口疼”,忙问:“怎么解?”
张玄从包里取出七枚铜钱,按北斗七星摆放在井台上,又烧了道“五雷符”:“今晚子时,你下井把那女尸挖出来,移到向阳处安葬。
记得用朱砂在她眉心点‘往生印’,再给胎儿超度...”他话没说完,医馆里突然传来瓷器碎裂的声音。
我们冲进屋,只见孙浩然扶着药柜站在地上,脸色煞白如纸,手里还攥着块碎瓷片——他的掌心被划开道口子,血珠滴在青砖上,竟凝成了紫黑色。
“浩然!”
我冲过去按住他的手,触到他脉搏时心里一惊——那脉搏虚浮无根,像片随时会被吹走的落叶。
孙启明拿出银针要扎“内关穴”,张玄却拦住他,翻开孙浩然的眼皮看了看:“不用针,是阴煞入体。
去拿附子理中汤,再加三钱朱砂...”我望着窗外渐暗的天色,手心全是冷汗。
六年未见,曾经追着我跑的胖小子如今瘦得脱了形,眼窝深陷,嘴唇发青,分明是被阴煞缠了半年。
张玄说的没错,这趟回来,怕是有场硬仗要打了。
子时三刻,我蹲在井边,手里攥着洛阳铲。
张玄在井口摆了盏七星灯,灯芯跳动不定,映得他脸色铁青:“下去后先找尸身,若见胎儿缠着脐带,立刻用黑狗血泼上去。
记住,卯时前必须完事,否则...后患无穷。”
我点头,握紧铲子跳进井里。
井底淤泥没到膝盖,腐臭味熏得人作呕。
借着月光,我看见角落里蜷缩着具女尸,长发遮住脸,肚子高高隆起,果然如孙启明所说。
刚走近两步,突然听见“咔嚓”一声——是骨骼错位的声音。
女尸的头缓缓转过来,眼窝深陷,嘴角咧开,露出青白的牙齿。
我握紧铲子,指甲掐进掌心——这是“僵尸初醒”的征兆,若让她起了尸,今晚谁也别想活着出去。
“得罪了。”
我默念一句,抡起铲子砸向她心口。
淤泥溅起,露出她胸口插着的半截剪刀——原来她是用剪刀刺进心脏而死,难怪怨气不散,化为胎煞。
“天圆地方,律令九章...”我念着张玄教的镇魂咒,用黑狗血泼在她眉心,“阴魂归位,勿扰生民...”女尸突然发出低吟,肚子里鼓起个小包,像有什么东西在动。
我浑身冷汗,颤抖着摸出朱砂,正要往她肚子上画符,井口突然传来张玄的喊声:“不凡!
快上来!
有人来了!”
我抬头望去,只见月光里晃过几个黑影,手里提着锄头、镰刀,正是赵家村的村民。
领头的是王瞎子,他拄着拐杖,阴恻恻地笑:“张不凡,可算等到你了...”身后传来布料撕裂的声音,我转头一看,女尸的肚子己经裂开,露出半只青紫色的小手。
井外的脚步声越来越近,张玄的七星灯突然熄灭,黑暗中传来罗盘摔碎的声音——这下糟了,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
这一夜,注定无眠。
而我和孙浩然的命运,也在这口阴井里,悄然埋下了更深的伏笔。
同类推荐
 未婚妻怀孕后,我和别人闪婚了(林硕宋淑语)完本小说_全本免费小说未婚妻怀孕后,我和别人闪婚了林硕宋淑语
未婚妻怀孕后,我和别人闪婚了(林硕宋淑语)完本小说_全本免费小说未婚妻怀孕后,我和别人闪婚了林硕宋淑语
玖日故事
 小满姑娘柳子稷陆景明免费小说_完本免费小说小满姑娘柳子稷陆景明
小满姑娘柳子稷陆景明免费小说_完本免费小说小满姑娘柳子稷陆景明
玖日故事
 不当大孝女后景川容羽热门的网络小说_完整版小说不当大孝女后(景川容羽)
不当大孝女后景川容羽热门的网络小说_完整版小说不当大孝女后(景川容羽)
佳期如梦
 沈临渊萧青月(回国后拯救被拍卖的姐姐)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
沈临渊萧青月(回国后拯救被拍卖的姐姐)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
玖日故事
 死后第五年的日记徐绾绾顾淮川免费小说全本阅读_小说免费完结死后第五年的日记徐绾绾顾淮川
死后第五年的日记徐绾绾顾淮川免费小说全本阅读_小说免费完结死后第五年的日记徐绾绾顾淮川
玖日故事
 天劫返世应不染陆霖洲完结版免费阅读_天劫返世全章节免费在线阅读
天劫返世应不染陆霖洲完结版免费阅读_天劫返世全章节免费在线阅读
玖日故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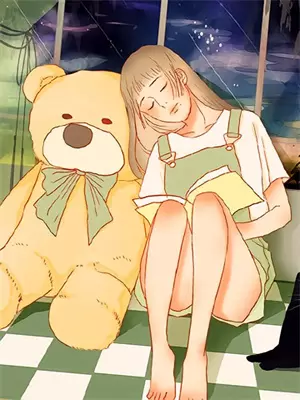 失去真心沈梵天桑禾晚免费小说全集_免费阅读无弹窗失去真心沈梵天桑禾晚
失去真心沈梵天桑禾晚免费小说全集_免费阅读无弹窗失去真心沈梵天桑禾晚
玖日故事
 这次换我来当爸爸(张漾张漾)完整版免费阅读_最新章节列表这次换我来当爸爸(张漾张漾)
这次换我来当爸爸(张漾张漾)完整版免费阅读_最新章节列表这次换我来当爸爸(张漾张漾)
佳期如梦
 枝卿江青月(亲生哥哥为了假千金,将我放血丢进深山)免费阅读无弹窗_亲生哥哥为了假千金,将我放血丢进深山枝卿江青月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
枝卿江青月(亲生哥哥为了假千金,将我放血丢进深山)免费阅读无弹窗_亲生哥哥为了假千金,将我放血丢进深山枝卿江青月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
玖日故事
 被污蔑抢了假少爷的命数后小远沈如远最新章节免费阅读_被污蔑抢了假少爷的命数后全集免费阅读
被污蔑抢了假少爷的命数后小远沈如远最新章节免费阅读_被污蔑抢了假少爷的命数后全集免费阅读
玖日故事







